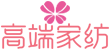这些平素最不解“风情”的女人们,却变成一群离“风情”最近的人。她们把平淡的生活织进针线,做出的情趣内衣就是曾经纳过的鞋底子,做过的眼罩,栽过的稻秧,和情欲毫无关系。
门口的大婶把一件红色透明短纱裙穿到模特身上,胖乎乎的手指头拽了拽飘起的裙角,又捏起V领的两个边微微往起提。摆弄好了,她从蓝白点的围裙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模特拍了张照片发给了老板。
这是一家位于灌云县东王集镇小巷子里的内衣制衣厂。工位上散落着五颜六色的丁字裤,一抬眼就看到穿着三点式、护士服、红肚兜的塑料模特。
在江苏灌云县的伊山镇和东王集镇,无论是随手打车遇到的出租车司机,还是路边种菜的大娘,他们都骄傲地说,“我家媳妇就是做这个的”。酒店的保洁阿姨羡慕已入行的姐妹,“我是不会做,要是会我也去做啦”。
三月的苏北,制衣女工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厚棉衣,用一针一线缝制着世界上最便宜的情趣内衣。这些衣服将出现在世界各地。
而这些平素最不解“风情”的女人们,却变成一群离“风情”最近的人。她们把平淡的生活织进针线,做出的情趣内衣就是曾经纳过的鞋底子,做过的眼罩,栽过的稻秧,和情欲毫无关系。
在某网站“情趣内衣”的搜索栏中,各种热辣的内衣名目琳琅,按销量前10名的店铺里,有7家显示来自江苏灌云,最高的一家90天内售出2万件。
灌云是个人口100万的苏北小县,距离连云港市区约40公里。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回乡的打工者把县城挤满,一位骑电动三轮车拉客的师傅抱怨,平日不到2分钟就通过的向阳大桥,堵了整整15分钟。
节后,街头巷尾大大小小的“服装厂”门口纷纷贴起火红的招工告示某某内衣服装厂招收缝纫工,工资4000-6000元左右,每月15号结账。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这里就靠情趣内衣。”整个下午,冬妮弓着背坐在缝纫机前,头半缩在鲜红的袄子里,只露出侧脸。若不是梳在脑后的头发留下挑染过又褪色的痕迹,看不太出33岁的年纪。
她把丝带捏成一个蝴蝶结的样子,匝在黑色低领半透明内衣的胸口,5秒钟一个,除了两只手不停地忙活,身子一动不动。这个姿势,她已经保持了3个小时。
丁字裤包三个边1毛钱,耽误20秒就少挣1毛。她手里这件新款内衣,手工费1块8一件,一天做100件。卖出去的批发价大约8块,网店挂出的零售价大约28块。如果卖到美国,仅批发价就有8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0块钱。
冬妮终于站起来,抓起一把工作台上刚做好的黑色透明蕾丝内衣,塞进草绿色的麻袋,递给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老爷子每天来这里拿些内衣回家剪线头。另一个女工抱起刚做好的厚厚一摞睡裙装进篓子,问冬妮做了多少件
80件,100件,150件她们扯着嗓子在高分贝的缝纫机噪音里互相报着完成的件数,就像在宣读战利品。
对面仓库里,靠近楼梯口的四排货架已经空了。冬妮的老板雷丛瑞说,订单已经接到今年8月份,据他介绍,灌云县30岁至45岁的人一共有大约10万人,女性占pg电子平台一半,而做情趣内衣的女工就有2万。
一件情趣内衣先由设计师画样式图,通过电子邮件和老板确认后发给大裁缝。大裁缝按照图片缝制样衣,再派给冬妮她们,照样衣复制。蕾丝、网纱、白布条、黑丝带这些材料,由裁剪工根据制版师的尺寸剪好,被冬妮们拼接成网上的“爆款”。
冬妮她们被当地人称为“机工”,不负责设计和剪裁,唯一的工作就是在缝纫机上操作。一个机工说,“我们不生产内衣,我们只是情趣的搬运工。”
“对你们来说,这是性感什么的,”冬妮说,“但我们只看包几个边,匝几道工序,然后算工钱,没人喜欢新款。”她们对新款的衣服结构不熟悉,比老款做起来慢。她手里这件1块8的,一天如果少做20件,就少赚36块。
伊山镇的一家制衣厂是菜市场后面的一块空闲地改造而成,绿色的塑料大棚取代了屋顶,挂在棚顶密密麻麻的吊扇没有转,却仿佛已经闻到了夏天的汗味。
新的工厂想开在城里已经没了地方,后入行的人只能把加工厂开在乡下,雇农村妇女一边带孩子,一边缝纫。
在灌云,大大小小的工厂不下七八十家,但能自主开发设计能力的工厂不超过5家。低端为主、利润低、批发走量是主要的经营模式。
“接的订单越多越赚钱,只要工人能做出来,货供给得上,就能赚钱。”雷丛瑞说,“我们这里是生产的源头”。
他厂房最靠里的几排货架编号以8开头,表示2008年。那是他们自主生产的第一批货,当时还在读高中的他,成了镇上第一个开网店卖情趣内衣的人。
第一批情趣内衣从广东进货,放在店铺里和暖宝宝一起卖。慢慢地,雷丛瑞和母亲萌生了想法“买别人的还不如自己做,这东西总共没几块料子,一块布穿几根绳子,能有多难?”
客户要什么款式就做什么,看网上哪个好就“借鉴一下”。作为一个和服装设计完全不沾边儿的门外汉,想做哪个款式就照猫画虎地剪,然后往自己身上套,尺寸合适就让工人做。他的仓库里现在还有2008年做的一条内裤花朵一样的粉边裹住硬硬的白纱,纱网的网眼大得像苍蝇拍。
雷丛瑞在办公室处理英国客户发来的邮件,寄过去的样品下胸围处的扣子系不上,需要重做。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那会儿供不应求,多丑也能成爆款。国外越露越容易爆,国内越含蓄越容易爆。”
从去年开始,1991年出生的雷丛瑞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生产模式,也有些担心被更加年轻化和个性化的店家超越。
雷从瑞现在每天关注b站,也加入了一些95后、00后的QQ群,最初只是想知道十年后的用户现在喜欢什么,“结果发现他们已经在购买了。”学生一放假销量就下来,一开学就猛增,已经成为各家工厂老板的共识。
一年前,他在贴吧里看到一个学生喜欢的店,现在已经从皇冠做到了金冠,主要推荐的是“二次元的款式”。这个91年的“老年人”在群里很不受欢迎,只因为说了一句“顶”,就暴露了“非二次元老年人”的身份,只好默默潜水不敢吱声。
“不过,也是杞人忧天了。”他现在最迫切的希望是招工,完成订单。至于收入,“一年下来七位数吧。”
尽管这些女工们拥有足以骄傲的生产业绩,但是对“衣服做给谁穿”、“自己会不会穿”的问题却格外警惕。
70岁的大娘坐在圆板凳上给白色“护士服”剪线头,听到这个问题扭过头去,和其他女工讲起了家乡话,似乎以“听不懂”来遮掩羞涩。
她伸长胳膊把衣服往远处拿,眯起眼睛盯了几秒又拿回眼前,空剪了两下,袖口的白线头还是没有掉下来。她住在七八里外的农村,除了麦收时忙一季,一年到头没有别的事情做,来厂里动动剪刀,一个月能赚将近2000块。
“谁穿的?反正我们不穿。”旁边粉衣服的大姐凑上来,拿着手里刚做好的镶白边的透明三角裤,“我送你一条,你敢要吗?”她和刘云,两个40岁人的笑声脆生生地搅在一起,她们自称“过来人”,也就是已婚。
刘云从服装厂出来做情趣内衣已经七八年了。花袖套磨得掉色了,她2秒钟就把细线穿进针孔,右手食指反复游走于缝纫机的针尖周围。偶尔,她也会被针扎到,血一下子涌出来。
“本来机器上有个防止扎手的保护圈,我们为了赶工嫌碍事,一般都摘掉。”她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赶着去买这些衣服。
“打个比方,有人拿刀杀了人,你不能说让铁匠不打刀。”一位年轻的作坊老板这样解释他们的生意。这也成为了小镇人的共识,“她穿她的,我做我的”。
一开始卖情趣内衣,她很不适应。第一次有人问她穿哪款老公会喜欢,她觉得“这个人好变态”。
后来,她发现确实有人很认真地在问,“肚子上赘肉多不希望老公看见选哪款”、“胸小怎么办”,才知道普通人也会买这样的衣服,而且有男的买给老婆或女友,让她附上软绵绵的情话。
“2、4、6齐了,这是一套。”高秋霞的老公小声嘟囔着。四五米长的黑色蕾丝布料在桌面上铺开,他按高秋霞剪好的纸板模型在布料上画起弧度。
他手腕上的足金链子是高秋霞买给他的,“抬胳膊都累得慌,没办法,媳妇买的不敢不戴。”
高秋霞个子很高,热情爱笑,面对老公时却“像个泼妇”。她的小店名字是老公起的,是她的真名。
忙不过来的时候,他把父母拉过来帮忙。父亲站在旁边看着一家人忙乎,“我这种身份,怎么能干这个?”
不过,她自己的父母现在依然不知道她在做情趣内衣。“你的衣服有没有我们能穿的啊?”她只好搪塞,“没有没有。”出了灌云,这个职业还是让高秋霞说不出口。
和灌云人“不知道”、“没穿过”、“你问她”的回答不同,在北京上班的花花小金刚(网名)并不羞于谈论。她是一家导购网站情趣内衣的资深小编,夏天总是穿着吊带,“我卖情趣内衣的,整天裹得跟个粽子似的,卖得出去么?”
记者走访期间,只有一个女工承认自己穿过自己做的情趣内衣。“粉的,好看,只比普通睡裙稍微透一点点。”洗完澡对着镜子看看,“也挺美的。”
他是灌云县商务局负责电子商务的主任,他记得情趣内衣生意刚在镇上兴起时,灌云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确实不太好意思明面上扶持。”
渐渐地,大家发现这门生意不但实现了增收,还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加入进来。村民把料子带回家缝,不种地的时候就做工赚钱。镇上的工人也没有上下班时间要求,方便接送小孩,“做一件算一件工钱。”
县政府于是顺应趋势,鼓励当地人学习电子商务。“每年有2000个免费名额,我们从上海、杭州聘讲师培训怎么开店,怎么推广。”徐小舟说,时代越来越开放和包容,不一定要带着有色眼镜看,把它当成一种产业就好了。
据他介绍,目前灌云县情趣内衣网络销售市场在全国占比达到60%,厂家和销售网店超过500家,其中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超过15家。
但这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衣服档次偏低、同质化严重、厂房简陋、商家太多导致利润越来越低等。用工招工的难题也让厂家老板们头疼,“今天高兴就来,明天有事又不来了,管理很麻烦。”
徐小舟透露,随着产业发展,老城区的伊山镇已容不下更多的工厂。在县政府2017年至2020年的规划中,相邻的东王集镇将打造一个产业园,把商家聚集起来,目的是引进高端人才和品牌,建设规范化的厂房,提升产品档次。
徐小舟说,产业园取名“衣趣小镇”。“不限于情趣服装,还有家居服。这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吧。”
她盯着一个嘎啦嘎啦响的机器,1厘米宽的黑布带子从里面送出来。10分钟后,这些带子将被剪成小段,缝在内衣上的肩膀上。冬妮弄完,把它们装进篓子,准备回家。
之后的六年,她一直在南京的电子工厂上班。凌晨两点的夜班是她最难受的时刻,流水线旁,她整夜整夜地想女儿。尽管只有330公里路,但周末一般也不回家,“不敢回,舍不得加班费”。
“在外打工就一句话,没有尊严。”冬妮去年返回小镇,她一点都不留恋曾经去过的高级酒店、飘香的面包房和自动化的大工厂,“那是人家城里人的。”
现在,缝纫厂的工作按件计费,上下班时间自由,可以随时接送孩子,这是几乎所有女工打这份工的原因。
镇上那条不知通向哪里的盐河,河道上来往的货船依旧破破烂烂,但在她心中已经流成了母亲河。起初,家里的老人不愿她做这个,“伤风败俗的破玩意儿,苦不苦钱?”一听说苦钱,“哦,那做吧。”
“苦钱”,在当地方言里是“挣钱”的意思,百科词条解释它的原意为“辛苦地挣钱”。
“什么是生活啊?生活就是,羽绒服给孩子买600的,老公买300的,我买的200的。”冬妮想了想又说,“不行,还得买一件500的,串亲戚的时候穿。”
缝纫机停下来,屋里终于安静。苏芮刚柔交错的歌声从手机里飘出,混在喇叭的丝丝杂音里,让人仿佛置身上世纪90年代的南方工厂。
有人跟着哼起来,“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程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
本文由:PG电子模拟器家纺生活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