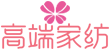“离散是为了重新在场”——带着这样的期待,今年三月播客「螺丝在拧紧」(以下简称「螺丝」)宣布进入暂时的停更状态。我们也在这个停更期和吴琦聊了聊告一段落的播客工作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螺丝」的主播吴琦,现担任《单读》主编,曾在《ACROSS 穿越》和《南方人物周刊》担任记者,并著有《把自己作为方法》和《多谈谈问题》等作品。面对媒体行业的转型浪潮,吴琦选择加入出版行业,继续在文化领域深耕。吴琦将自己比喻为媒体时代的“活化石”,他保留了在传统媒体工作时所养成的采访技巧——将对话放入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框架中,并将其适当调整后,应用在播客的制作中。
这档在疫情时期诞生并走到当下的播客,记录了吴琦与嘉宾们的一次次畅谈:与戴锦华、余苗红聊母女关系,与项飙讨论俄乌冲突,与熊阿姨聊三年后重返世界的旅途……它从出版业出发,将触手伸向文化产业的友邻,并对社会议题保持着关心,也将小众但有意义的话题带入大家的视野,将讲述和讨论作为困境的出口。
在接受访谈的两天前,吴琦与友人完成了一期关于巴以冲突的播客录制,这是宣布暂时停更后的第一次复更。在六月和七月,「螺丝」陆续推出了三期播客,讨论从东亚文化出走、欧行漫记和反脆弱等主题,持续创造有机的话语。
与此同时,作为听众的我们也清晰地感受到主播吴琦的细微变化:旅欧三月后,他似乎更加珍视日常生活,放下一些自我戒备,更松弛自在地感受生活。工作、社会、时代这些宏观议题,或许并不比两道彩虹和一缕阳光更重要。
我们有太多想和吴琦聊聊——关于这档播客和表达媒介,关于如何“把自己作为方法”,关于过去三年和我们逐渐“拧紧”的生活,个体该如何放松,以及对文化传媒行业仍有热爱的人怎样找到空间,坚守阵地,不忘却地向前。
Q:「螺丝在拧紧」的播客名称本身应该是一本恐怖小说,描写人心里的恐惧情绪像“没有疆界,无助使人颓丧,心像旋转的螺丝,越拧越紧”,为什么选择这个名称作为播客,会有什么联想吗?
A:这个播客实际上是疫情催生的产物。疫情初起时,大家都感到恐慌,许多线下活动不得不停止。作为一家小规模的文化单位,书店也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当时,我们团队一起探讨如何制作更多线上内容。虽然播客很早之前就已经流行了,但我之前并未觉得必须去做。然而,在那种特殊时期,我感到了一种迫切的需要,也想把当时那种紧张、需要个体不断自我调动、处于防御应激状态的感受表达出来。
于是,在思考这个方向时,我回想起自己读过的书,尤其是那些我最喜欢的作家的作品。突然,「螺丝在拧紧」这个名字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即使你不知道它是一本小说,不知道它是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你也可能想象出那个场景,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哪怕不在危机状态下,也具备的一种紧张感和要调动自己去面对一件大事的感觉产生共鸣。
至少现在,当我们提到「螺丝在拧紧」,我们认为它作为一个比喻,象征着我们正在拧紧的螺丝钉,这个比喻似乎是成立的。
此外,关于这本小说本身,它之所以被记住,就是因为它有多种解读方式:它到底是一个恐怖故事,一个灵异故事,还是一个犯罪故事?或者是作家的心理投射,还是一个疯狂的故事,即作家本人疯了……许多评论家都有不同的解读,因为在小说中并没有明确写明,所以这个标题本身就包含了开放的意义空间。我觉得这与我们在文学创作、阅读以及经营书店过程中所追求的理念是相契合的。
Q:「螺丝在拧紧」是一档对谈类播客,《把自己作为方法》也是一本对谈书籍,在筹备中有何异同?可否举例谈一谈您是如何筹备的?
A:两者相比,实际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我的工作方式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之前在传统媒体(如杂志)工作时的采访方法。我过去的采访方式并不局限于围绕五个W(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进行提问,而是尝试将对话纳入我自己构建的理解框架中。
后来,我意识到只需稍作调整,就可以将这种采访方式应用到播客中。我希望播客的对话是有结构的,能在某个议题上进行深入、专业的探讨,同时展现出嘉宾的独特性——他们看待问题的独特方式和风格,这与轻松、随意的聊天式播客不同。
我常说自己像是传统媒体时代的“活化石”,在这种新的媒介形态中,我融入了自己所经历和坚持的传统媒体采访方式。这基于我的学习和工作经验,是我掌握的基本职业技能。
举例来说,我曾与和进行过对话。在与他们不熟悉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双方都对我们谈话的顺利程度感到意外。为了与不熟悉的人进行有效沟通,我需要了解他们的过去,进而提出一些具体而细小的问题。比如他们何时会感到不高兴,以及如何应对这样的情绪等。
我记得在准备与韩夏的对话时,她说看到提纲后想哭。这可能是因为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很少对他人表现出全面的兴趣。通常情况下,人们只对他人身上对自己有用的部分感兴趣。而在与吕植讨论动物保护和自然问题时,我带入了个人对这一议题的情感,而不是仅仅是浅表地讨论科学问题如何在社会政策中得到解决。
Q:无论是在「螺丝在拧紧」抑或是在和项飙老师的对谈中,“把自己作为方法”一直是您基于个人经验看待宏观世界的方式。对于其他不同职业、不同生活处境的人来说,这是否还是一种可供参考的方法论?
pg模拟器
A:我认为我们的关注点可能主要还是集中在与文化工作相关的群体上。从创立之初至今,我们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位:作为一个由书店衍生出的播客,我们更多地聚焦于文化领域,涵盖了传媒、出版、艺术、电影等多个方面。这个定位界定了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希望呈现的是这一群体对世界的思考和反应,让更多人了解文化工作者的思考以及他们的想法为何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那些认为人文学科或新闻“无用”的观点的反驳。
在目前的环境下,将文化作为全职工作可能很困难,但我们不希望大家因此放弃自己的兴趣,或者成为对立面的批评者。如果不能完全以文化为职业,我们还能以什么方式与文化保持联系?无论是作为读者、听众,还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甚至是一个小型创业者,比如开一家咖啡馆,都可以是文化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这个社区能无限扩大,也希望能通过播客为对文化行业感兴趣的人提供启发,特别是当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找不到新方向的时候。
Q:在您的第一期节目中,您提到对这档播客的期望是像一个“思想上的日记”。能否详细分享一下您对这个播客最初的设想和期待?目前节目的实际情况和您最初的预期有何异同?
A:我最初并没有设定太多具体的预设和期望。我们坚持把每年的播客作为一个季度,每个季度都给自己留出休息和调整的时间。每个季度的选题方向和角度都会有所变化。例如,在第一季,我们主要把它当作一本书来制作,与来自不同行业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工作经验。到了第二季,我们开始尝试从文化角度回应一些重大议题,比如疫情或国内外的新闻事件。到了第三季,我们引入了像愉悦清单这样的轻松内容,这既是响应观众的呼声和期待,也是希望让自己轻松起来。
总的来说,每个季度我们都设定了明确的选题方向,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问题。然而,在第三年的时候,当我打算继续深入讨论严肃话题,特别是与疫情相关的话题时,我遇到了一些听众的直接反对。他们认为我在原地踏步,但这些话题对我来说依然非常重要,是我真心想要表达的观点。
这就导致我和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最初我将其视为批评,但后来意识到这可能不仅仅是对个人或节目的批评,而是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这种张力源于我感知到的“应该做的事情”与观众内心感受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真实问题。我认为疫情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段,我们需要通过它来探讨社会问题,并开启对新议题的讨论。
A:疫情是第一次在我的眼前,以国家为范畴,在一个广阔地域内展示出现实的残酷性。此前我们对社会的想象很多时候来自书本、历史、传说和别人的经验。你可能读过非常残酷的历史,但是无法完全想象和共情置身其中的感受。这意味着你没有真正理解那段历史,没有理解那段历史当中人的反应。
但是疫情把真正的现实丢到你面前,比如说,你突然不能出门,不能下楼,不能出小区,你也得不到你想要吃的东西。即便是基本的温饱和出行自由,在疫情面前,也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光是这一件事情就值得我们想很久:整个社会制度是如何运作的?社会中某个具体的位置上具体的人,又是如何做出决定的?这些具体的决定,会变得难以想象,可能会和你的一些基本设想不太一样,让你意识到我们没有想象得那样强大,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没有被触碰到,而且可能会在之后再次出现。我们要对话甚至抵抗的其实是这样一些本质上有待改善的东西。
这是持续要去思考的:为什么会是这样,以及为什么这样的机制在今后可能还会被调动。当时鲍曼或者阿伦特去反思某个历史事件的机制——悲剧发生了,所有人都很悲痛或者很愤怒。但是造成事件的那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常反常的举动?或者,这真的反常吗?还是给一个人一定的条件,Ta就会变成这样?
对于我这一代人,疫情是我们人生观、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很重要的参与因素,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教育。它使我们能够真正进入到知识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所以我觉得它会改变很多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知识、对于历史、对社会基本的感受,包括我们的决定。
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大浩劫,有时候是一场战争,有时候是一场瘟疫,我们只不过刚好赶上了它。历史就是这样运动的,在一些时刻它会暴露出非常狰狞的面目。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我们不能假装没有看到,背过脸去。尤其是号称自己做文化工作的那部分人,那这就是你工作当中应该看得到的题目,一个巨大的题目,必须去面对它,或者以它为起点重新构想你的工作,而不是假装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太阳的阴影,它过去就算了。
Q:你也提到,「螺丝」是疫情当中诞生的播客,在疫情当中那么多体验都扑面而来,那它会怎样影响这档播客的形态?包括您也提到,应对疫情这段经历可能是这些文化行业里面必须承担的一个东西,那「螺丝」会有意识地承担这样的功能吗?
A:我觉得一个很具体的情况就是,现在我想要聊疫情这个话题,基本上就意味着「螺丝」会失去听众。所以在做了很多次尝试之后,我觉得直接反思疫情这条路行不通。可能另外一条路是可行的:去反思疫情暴露出的各种社会问题背后的原因以及其他层面的影响。
比如我们这一期,背后是失效的政治机制与依然有主体性的年轻人对于世界的基本期待之间非常剧烈的冲突。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听,但是至少从我的角度,我好像找到了一种既能延续对疫情当中的问题的关怀,又聊得更深、更远的方式。
Q:当下还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返回到那三年的经验当中去回看才能找到答案的?
A:这个问题可能要分不同的行业或者领域来看。比如文化工作的领域会受到限制,还会有人不断新造一些词,比如“按下暂停键”这样一些看起来更接地气的口号,试图通过影响话语本身去影响人。这更说明了话语本身的重要性,反过来说明了文化行业的重要性。
文化行业即使没有直接的生产力,至少要生产有力的,或者是有机的话语。如果文化工业与工作被权力机构掠夺,这是对于一个行业的整个抹杀,电影、书之类的可能就仅供消遣,不能产生或者是直接讨论时代议题——因为它们进入不了话语空间。因此文化工作者要对这个前提有认识,有时候要致力于生产自己的话语。
作为做文化工作的人,我们要持续去想:我们觉得当下的社会有问题,那么如何去回应,怎么在话语层面去调动大家的参与讨论?项飙老师就是一个例子。比如他讲“内卷”,讲“附近”,这些词就能够调动起公众的意识。虽然这些词看起来都不是在反对什么,或者倡导什么,但是当人们讨论这些的时候,自然就远离了那些更虚伪的话语。所以对文化工作来说,我们要争夺的更多就是这个层面的话语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文化工作的确还是有很多可做的。
Q:您之前跟项飙老师的对话中多次谈到“附近”跟“远方”这两个词汇,其实我们能感受到一个趋势,在疫情前,大家会关注远方而会忽视附近。但是在疫情后,大家似乎发现对远方无能为力而回归附近和内心世界了。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A:在“回归内心世界”这一点上,我与项飙老师的观点存在一些差异。他强调“附近”的重要性,并明确表示他并不特别赞同“同温层”的概念。他觉得“附近”就是要打破同温层,你要跟和你自己很不一样的人去接触、去交往,这样才能实现突破。
然而,我认为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同温层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且重要的,它具有全球性——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很多方面有着高度的共鸣,无论是对世界的看法还是希望带来的改变。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拥有全球性的知识和框架体系,这使他们有能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出国,但拥有对世界的想象和视野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对“远方”有了想象,你对“附近”的决策和看法也会有所不同。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叫Halle(哈勒),这里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做了个展览,讨论争论与分歧。它把这个城市在过去的历史当中那些大大小小的纷争都汇聚在一起,小到一个公务员想要涨工资,或是邻居之间的争吵,大到战争、屠杀。这个展览把这些纠纷的文本资料都收集好,展示给大家看。你既可以看到在厨房中的争吵,也可以看到大的社会事件。这就是附近和远方的一种联结。
所以我认为,一方面,照顾好自己的小生活和对自己的附近保持高度的关注和参与是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对广阔世界的感知和好奇心。这两个也不一定是矛盾的,它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工作,我们应该努力将它们联系起来,实现相互贯通。
Q:您也经过很多次的媒介转换,比如说从传统媒体到出版,还有现在的播客。作为内容生产者,您和不同媒介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您会不会根据不同媒介的特点来调试自己的表达?
A:首先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对印刷物有执念的人,包括我在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我会用做一本书的方式去构想。这个习惯可能很难改变,因为我确信自己未来仍会以书籍或杂志的结构来想象自己的工作。我并不认为书籍和杂志已经过时或落伍,反而觉得这种方式非常有趣。与此同时,我所做的调整主要集中在提升口头表达能力上。实际上,这种能力的锻炼始于在书店举办的小型活动,比如新书讨论会、发布会,或是与作者的对话。
与此同时,我调整的部分不是很多,主要是调整自己口头的表达。其实口头表达的锻炼是从在书店里做小型的活动就开始了,比如一些新书的讨论会和发布会发布,或是跟作者的对话,这些都是对我的一种训练:要当众把脑海中的内容表达出来,还得有起承转合,并且兼顾现场大家的反应。在这个基础上,做播客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痛苦。
Q:您说过自己曾经是一个不怎么进行公开发言的人,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能够进行持续性公共表达的人。您如何看待播客在自己进行公众表达中的作用?在那么长时间的实践之后。您是否对公开表达和发声有了新的实践经验与理解?
A:播客是公共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同时社交媒体也是。之前我的社交媒体还是比较冷感的,但疫情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手里仅有的这些“武器”还是都要用上。但同时也会反思,未来如何让公共参与变得更有力一点。比如说,我可能参与对巴勒斯坦的声援,但我希望用更深入的讨论去揭露它背后的一些层次和我理解到的一些没有被讨论的话题,给公众增加一些可供讨论的文本。表态只是第一步,之后你要通过你自己的写作、研究、整理、访谈,去给中文世界制造更多的材料,参与塑造实际的讨论内容。如果我接下来还可以继续做公众表达的话,这会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Q:作为内容生产者,表达空间的缩减以及随之而来的紧张感或许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命题。这会如何影响这档播客和作为主播的您呢?
A:我认为,首先,这种紧张感源于我们自身,是我们作为具有基本感知和反思能力的人容易感受到的,这实际上是一个优点。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过分沉浸在这种紧张感中,因为有时它是我们自己放大的。尽管外部环境可能显得紧张,但在播客领域,我们一直拥有相对宽松的空间。例如,我们之前几期直接讨论疫情的内容至今仍被保留。
我们不应该过早地以为有的话不能讲,相反,我们应该经常鼓励自己,在能说的时候就多说几句。如果不能当着一百个人说,那就在小范围内当着十个人、两个人说。这其实也是一种训练,训练我们的能力和胆量,去试试那个言论世界的边界。
我们需要努力从身体记忆中排除自我设限,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无论是选择出国,还是与朋友进行更深入的交流,重要的是在一个你信任的环境中大胆地表达自己。说出来这个行为至关重要,因为一旦你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论有多少人听到,你的世界观都会发生改变。你会意识到自己有能力表达,你的舌头没有被别人拿走。
Q:您的回答让我回忆起在播客前几期的时候有听友向你们提问:播客是一次媒介撤退,还是一次媒介的拓展。想听听看你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A:可能现在我还是不会去回答。媒介的更替有一定的历史规律,从报纸杂志到电视电影,都是技术和社会心理推动的潮流。个人很难与这个潮流对战。当更多的人决定不看报纸的时候,那报纸就会面临消亡,或者以电子的形态才可能继续生存。播客在这个潮流当中到底是属于先锋的还是属于落后的?一是我个人回答不了,二是眼前留给我的选项就只有书店和播客,我觉得我不能回答。
当你们拥有选择的可能性的时候,你们选择去做电子媒介还是做杂志、做书,决定了这些行业未来会怎样。只有特别具体的个人的选择,才可能和社会潮流之间形成一个反方向的力量。所有人都去看电视,但是有一个人坚持拍电影,那电影就会因为这一个人存在——哪怕这个人只有一万、一千个观众,但是Ta的选择会留下来。所以我会觉得,我们改变不了潮流是什么,我们也不用去管它。你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媒介是什么以及未来有什么新的可能性。
Q:「螺丝」后面有推出“愉悦清单”“小地方”等风格相对轻松的一些栏目。「螺丝」的内核在“紧张”和“放松”之间,有进行过怎样的调试吗?
A:我觉得现在我还是在一个调试的过程当中。之前更多时候是在被日常更新的工作压力推动着走,没有真正紧张起来,或者放松下去。
我个人生活正处在一个慢慢放松的过程当中,之前「螺丝」说,放松是一种新的抵抗,我依然同意这个观点。但与此同时,不是瘫在沙发上就叫“放松”——那可能叫“发呆”或者是别的什么。放松其实需要更多地学习。怎样更好地让自己松弛下来,怎样找到一个可以跟更多人分享的放松之道?甚至“螺丝在拧紧”这个题目本身就没有给放松留下空间,螺丝一直在拧紧的话,那放松是什么意思?「螺丝」是否能够承担这种松紧之间的关系?我还要再想一想。
Q:感觉当下面对着许多的不确定和流动,个体的经验框架一直在遭受着一些大时代的冲击,然后重建,那么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
A:我的回答仅基于个人经验。目前我认为,尊重自己的感受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在需要全力以赴的时刻,还是在需要休息以恢复体力的时刻,我们都应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如何尊重自己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过去,我们主要学习知识,了解社会,学习如何适应社会标准。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常常被忽视。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比如选择吃什么、看什么,也都是了解自己的机会。
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这些问题只有我们自己能回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社会标准和压力,但只要我们内心有一个稳定的核心,就能更平和地面对世界,不易随波逐流。
把自己作为方法,首先需要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是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反思和持续的自我对话。“与自己的对话”是建立自己的方法的一个关键起点。
Q:访谈开始前,您提到的那种被迫陷入一种“自然卷”的状态我们深有共鸣,感觉好像一种紧张的气氛弥漫在周围,大家好像很容易就“拧得太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到哪里去寻找一些放松的空间和可能?
A:我认为,在真正放松之前,首先需要暂停手头的许多事务。过去,我们对白领工作的想象是,一周五天时间忙碌,周末两天放松,如此循环。但工作节奏慢慢变成了996,紧张占据了全部的时间,这时这种放松模式就不能持续了。
因此,学会暂停和退出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并不意味着完全退出生活和工作,而是要有勇气和能力去决定哪些事情可以停止,哪些合作关系可以终止,以及哪些人可以不再见面。我认为,做出判断和拒绝是实现放松的前提条件,这一点需要被明确提出。
尽管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你们生活条件较好,所以可以选择拒绝和放松。但事实上,文化工作者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优渥。而且,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定的空间。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勇于拒绝一些事情,放松的状态就会慢慢到来。否则,如果我们一直处于社会链条的压力之下,就难以获得真正的放松。
Q:您个人如何看待目前传媒行业整体的变化趋势?当现实世界与理想相去甚远时,该如何保守你的内心?
A:行业的发展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但我还是觉得,在夕阳的行业当中也有可能有一些朝阳的位置,当然可能已经所剩不多。一方面,我理解并接受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人最终可能选择不直接进入这个行业。他们可能会从其他行业开始,但同时保持对这个行业的关注。我依然认为他们也是这个行业的一部分,或者说,我愿意这样看待,把我们阵容想得更广大一点。
另外,即使行业面临困难,我们仍可以设想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例如,在个人生活和工作决策中,是否还有机会再撑开一点空间?或者,如果你目前从事其他工作,是否有机会向文化行业靠拢?如果你是一名广告策划者,或许可以考虑邀请作家或翻译参与广告制作,或者从文化角度出发进行创意构思。我相信,个人发展空间总是存在的,而且那些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人,很有可能会做出更大的成绩。当行业不再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时,那些依然在其中努力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认可。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机遇。如果你确信自己注定要从事这一行业,现在也许并不是一个糟糕的时机。
我也许不太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行业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可以说这样的话。对于那些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朋友来讲,现实可能还是会比较难。我也不想盲目鼓励大家咬牙坚持,但是世事难料,机会和挑战总是并存的,说不定,机会就降临到你身上了。
原标题:《「螺丝在拧紧」主播吴琦:调试再调试,为了在场的、有机的话语丨对话自媒体人》
本文由:PG电子模拟器家纺生活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