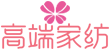海子是一个沉重话题。大概因为这种沉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下简称《面朝》)从中学语文必修教材被移到选修教材,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据说,教师们很难回答学生的疑问:一位如此热爱生活的诗人,怎么会走上不归之路?但是好像没有人探究,海子所热爱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意义。
海子的好友、诗人、翻译家西川说:“一个人选择死亡也便选择了别人对其死亡文本的误读。个人命运在一个人死后依然作用于他,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三十多年后,依然有许多人借助他的诗歌在思考。
海子本名查海生,1964年5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自幼在农村长大。1979年,十五岁的他以安庆地区高考文科状元身份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也从此开始文学创作生涯。毕业后先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刊工作,后转到哲学教研室任教,并随学校搬迁到昌平新校址。海子开设的美学课很受学生欢迎,在谈到想象时他曾举例道:“你们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1989年3月,他在河北山海关附近的一条铁轨上卧轨自杀,留下了将近二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论文。
海子当年在昌平的生活相当寂寞,也相当贫寒。有一次他走进一家小饭馆,对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老板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
海子生前,大量的诗得不到发表,便油印成册赠送友人,却被人频频抄袭见诸报刊,这令他郁闷不已。海子身后,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他、评论他、研究他,他的诗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学、大学教材。
许多诗人、批评家在文章中都提到,《面朝》是各地房地产商营销时最喜欢引用的文案之一,尽管他们的房子可能离大海很遥远,但他们肯定觉得这首诗足以诱惑人们慷慨解囊。
海子生前自称“物质的短暂情人”,若他九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但他是不会抱怨的,因为这就是身为诗人的命运,因为这就是加缪《西西弗的神话》里说的:“如果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就不会有更高的命运,或者至少可以说,只有一种被人看作是宿命的和应受到蔑视的命运。”
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每个人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我们可能不写诗,可能不想成为诗人,或者,不想成为海子那样的诗人;但面对这样的诗人,面对这样的写作,首要和基本的态度是尊重:尊重他人的选择就是尊重自我的选择,尊重他人选择死亡就是尊重我们还在坚守生命。在此,西川三十多年前的话仍然值得深思:“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宁肯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有鉴于此,我要说,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和时代生活中的种种黑暗、无聊、愚蠢、邪恶真正较量一番。”
大家都知道“诗无达诂”的说法。“达诂”指确切的训诂或解释,意思是说,每个人的生活阅历、思想修养和文化程度不同,对同一首诗往往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个成语可以用来表述解释的相对性和审美的差异性。我们对诗歌所作的解读,广义上都可称为“误读”;甚至可以说,没有“误读”就没有诗歌欣赏和批评。
但有两种误读需要警觉,一是望文生义,信口开河;一是拘泥于“先存之见”而不自知,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未能觉察自我的偏见,对文本的“异己性”或“他性”缺乏敏感。这两种误读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离开语境,自说自话。因此,对同一个文本固然允许多解并存,但每一种解释都应在文本中求得验证。
朱自清20世纪40年代就主张,“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诗人、翻译家梁宗岱也曾谈道,有些批评家娴熟于阐发原理,一当引一句或一首诗作例证时,“却显出多么可怜的趣味!”原因无非是批评家的理论是“借来的”,他并不了解自己说的话或讨论的问题。
学者、批评家蓝棣之也提出,“最好的解诗方法是一句一句地解,一行一行地解,一句一行都不可跳过,只有这方法可以把任何一种风格的诗解通。解诗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解释它的大概意义,这是最能胡说的了,但这种胡说往往被说成是接受理论的方法,或什么‘诗无达诂’”。可惜,现在肯用这种笨办法、肯下这种笨功夫的人不多。
诗题“重建家园”是个很普通的短语,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现代诗歌一般主张诗歌语言是对日常用语、科学语言的疏离,俄国也倡导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海子的诗题似乎反其道而行之。当然,诗人用它作标题,不可能是随意的。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对这三种语言形态不宜作静态理解,它们之间存在转化,尤其是前两者。最早的诗歌使用的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劳作的语言,今天的许多日常用语也是由诗歌语言转化而来,只不过由于使用频繁,它们已不再被视作诗语了。
“重建”意味着原有家园的毁坏、丧失;没有家园的人自然不存在家园的丧失,也就谈不上“重建”问题。那么,是什么样的家园被毁坏而需要重建呢?
“家园”是这首诗的核心词语(意象)。如果把它从诗歌语境中移出,既可指物质家园,也可指精神家园—注意,当我们依凭习见做出如此分辨时,已在动用“智慧”了。不妨设想一下:在远古蛮荒时代的人的头脑里,“家园”意味着什么?会有现代人这样条件反射似的“分辨”能力吗?
有评论者将这首诗与《面朝》联系起来,认为它们表达了同一主旨,即对尘世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并进一步指出,这首诗更为明确地传递出诗人要放弃虚无缥缈的高迈理想,回到现实的意图,“显示了对自己既往追求的一种反思和否定”。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面朝》是否表达了对尘世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从它的最后两句诗,特别是从“我只愿”形成的转折意味可以看出,诗人是在衷心祝福亲人和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在尘世间拥有各自的幸福,他依然有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在为他人祝福的同时,他也希望他人能为他所追求的幸福而祝福。前面提到的那些房地产营销者,看中的恰恰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理想而非写实的成分,是诗句中营造的、犹如世外桃源般的美妙意境。这一点他们是对的。
那么,认为《重建家园》传递出诗人要回到现实的意图,除了误读《面朝》,也误读了这首诗中的“家园”二字。解诗者按照自己的先存之见或固有理解,非常“自然”地将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对立起来,进而依据下文,将“家园”理解为物质家园,而没有觉察这其中有什么问题;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理解可能正是诗人想要打破的现代人的思维怪圈。每个人的每一种看似“自然”的想法或做法,实际上都是一种“不自然”的产物,是被现代文明/文化塑造成形的。上述解读的背后,体现的是现代人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习性。
按照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观点,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一开始就是隐喻的,即偶然、不确定的。他让我们设想,远古人类最早是用肢体动作、表情和简单的音节、音调等进行交流,这个过程异常艰难。当这些传情达意的元素通过反复交流、磨合达到暂定的一致时,包括语言在内的本义开始形成,然后又在本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隐喻,如此循环往复。他把这种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珊瑚礁:旧的珊瑚不断死亡,而成为新的珊瑚生存的“家园”。所以,海子诗中的“家园”不能单纯地理解成物质家园,它本身是个深刻的隐喻。它和大地、太阳、月亮等一样,属于人类使用的最基本的语词,是所有语词中的词根部分,积淀着很深的文化意蕴。我们下面分析诗歌时再具体展开。
诗的首句就引发了疑问:为什么是在“水上”?为什么是放弃“智慧”?水与智慧有关联吗?
乐,仁者寿。”钱穆注曰:“水性活泼流通无滞碍,智者相似故乐之。山性安稳厚重,万物生于其中,仁者性与之合,故乐之。”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与“知(智)”确实有关系。此外,水能引起人对时光、生命的思考和探询。孔子曾在水边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许,没有什么比“斯”更能引起人对“逝”的感喟;逝,消逝、丧失,一去不复返。这与这首诗因为丧失家园而重建是紧密呼应的。我们同时联想到,远古人类逐水而居,水因此成为人类文明发源地的重要标识,四大文明古国皆是如此。而文明与智慧是相伴相生的。
这句也提示我们,家园的丧失与水有关系。水是生命之源,亦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旧约 · 创世记》载,耶和华造亚当之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又引河水滋润它。亚当、夏娃的子孙传到挪亚一代,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便起了毁灭之心,使洪水泛滥。唯有挪亚蒙恩,受命造方舟躲避了洪水。
因此,不论从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元典来讲,水与智慧都有紧密关联。现代人的智慧又承此而来。放弃智慧之后,是否要做一个仁者,诗人没有言明。仁者,仁厚之人,包容万物,喜与万物同在。这与诗的意旨是吻合的。
有人说,“长空”象征高迈理想、不切实际的幻想,诗人以“停止仰望”来表达对以往空想的否定,从而回归世俗生活。实际上,这一句接上句而来,表达的仍是“放弃智慧”之意。比如,楚人屈原仰望长空,在《天问》中向老天一连发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表现了诗人对自然、历史、社会深思熟虑后的见解、质疑。也就是说,人在仰望长空时,往往会引发深沉的理性思考,激起内心奔放热烈的情感。在海子看来,理性思考即智慧,要“放弃”;奔放热烈的情感需要“停止”—这一句的重心不在“长空”这一对象,而在“停止仰望”这一动作。全句在说,即使家园的毁灭是由上天引起的(如《旧约 · 创世记》所描述),也不要追究、抱怨,而要平静地接受这一切。
生存不仅意味着幸福,也意味着苦难和屈辱;生存意味着承担,既承担幸福,也承担苦难和屈辱,如诗人所言,“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生存也意味着平静;那些意识不到“人类的秘密”的人,自然无法做到平静。
第一节中诗人表达的是,经由“放弃”而终获平静。人只有放弃智慧和沉思,直面生存,才能意识到生存即承担,“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因之,生存即平静。
第二节首句中,诗人为什么使用“洞察”而不使用“观察”?洞察之洞,即深远、透彻之意。洞察需要沉思和智慧;而生存是何面貌,大地已完全呈现,并不是人借由深沉、理性的思考,用语言可以表述的。表述往往是词不达意的。我们只须面向生存本身,回到大地,感受大地。
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诗人为什么不直接说“来重建家乡(家园)”呢?这两句表述在意义上并无差异,区别在于,原诗语句重心落在“屋顶”上;若作修改,其语句重心则可能在“重建”,也可能在“家乡(家园)”上。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将阅读者的视线牵引到“屋顶”上呢?
“屋顶”自然指代的是家。甲骨文中,“家”这个字上面是“宀”(音mián),表示与室家有关;下面是“豕”,即猪。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多在屋子里养猪,所以房子里有猪就成了人家的标志。屋顶的重要在于它能给人以庇护,因为它的功能正是用来承受的:既承受阳光雨露,也承受风暴雷电。而幸福和痛苦也都是人需要承受的。
第三节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点明诗意,再次强调,沉思和智慧对于生存本身没有什么影响。生存类似于道,道若可道,则非常道,而道法自然。生存之道是不可言说的,沉思和智慧并不能解决生存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这里,诗人的生存观有老庄哲学的影响,带有宿命色彩。简单地说就是不要去问,只管去做。
熟悉海子诗歌的人都知道,麦粒是其诗歌的核心意象,表达着他作为农民的儿子对乡土中国的眷恋,有评论者因此称他为“中国农业社会最后一位出色的抒情诗人”。某种意义上,麦粒维持着中国社会和人民几千年的“生存”;中国长达数千年超稳定的农业社会结构形态,也在根基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大地是诚实的,因为它不欺瞒,使人喜也让人忧,使人生也让人亡—它按自己的道运转。
前面说过,生存之道不可言说;不可言说即缄默,也即不要沉思不要探究。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又说:“确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这是自己表明出来的;这就是神秘的东西。”这几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语言是无力的,语言与现实亦即生存之间存在鸿沟。“保持缄默”,就是以自己的诚实回报了大地的诚实。
那么,如何理解“幽暗”在诗中的含义呢?缄默即不思不问,浑沌一体。幽暗是天地鸿蒙之初的状态,也是人未开化、未发蒙的状态。这让人联想到《庄子》所讲浑沌开七窍的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幽暗是浑沌的另一种说法。按庄子的观点,人在浑沌时不思不问,是最幸福的;一旦七窍皆开,则会死去。《旧约 · 创世记》中夏娃在伊甸园偷吃善恶果的故事,与此类似。耶和华曾吩咐亚当、夏娃,园中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唯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但在蛇的一再引诱下—
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二人吃善恶果之前,同样处于浑沌状态:没有智慧,不辨善恶,不知羞耻。但他们却因为有了智慧而受到耶和华的审判,并被逐出伊甸园。亚当所得的审判是:“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从第一节到这一节,诗人一直在探寻的是生存的意味,亦即“人类的秘密”。在他看来,人应当回到大地,以劳苦所得的收获奉献给大地。人是大地的子孙,来自大地也将归于大地。这就是人的诚实本性。“两手空空”使诗人愧对大地(他在多首诗中反复表达过这种情绪),而对此所作的任何辩解都是一种丧失本性的堕落。海子这首诗里体现的“反智”倾向,与老庄哲学是一脉相承的。至于这首诗是否有《旧约》关于人的“原罪”意识的影响,仅凭上述分析,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不过从我们引述的材料中,还是可以看到其中的关联。许多诗人、批评家指出,海子后期诗歌在语言、结构、寓意等方面,都受到了《新旧约全书》的启示,是他追求“大诗”理想的一种体现。海子离开人世时,随身携带四本书,其中一本是《新旧约全书》(其他三本是梭罗《瓦尔登湖》、海雅达尔《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
炊烟袅袅升起,这是温情动人、素朴洁净的乡村画幅,越千年而不变。炊烟将阅读者的视线再度牵引到屋顶,定格在大地上的家园。
如同炊烟一样,果园对应着家园。这同样让我们联想起《旧约 · 创世记》传说。最初人类居住的伊甸园,就是果园(如前所说,此果园与水、善恶皆有关)。洪水过后,挪亚做起了农夫,也是种果园(栽了一个葡萄园)。诗人赋予果园(家园)以人的灵性;大地和人一样是上天创造之物,皆有灵性。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听到果园的“静静叫喊”呢?贴近大地的人,和大地同呼吸共命运的人。在大地上汗流满面的劳作的人有福了。
最后两句近似格言,流传甚广。如果把它们从全诗中抽出来,可理解为:我用双手劳动,付出了努力,无论是否有收获,无论收获大小,都可以问心无愧,无怨无悔—这与流行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观念非常合拍,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这种理解当然不错,但还需要回到文本语境中去品味。
回溯全诗,这两句是说,沉思和智慧并不能揭示生存的秘密;思之弥深,失之愈远。既如此,人靠什么获得对生存的秘密、大地的本性的理解呢?靠心的体悟、顿悟。心即悟,悟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庄哲学的重要概念。如前所述,生存类似于道,道是什么?《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总之,道是恍惚混融的,是形而上的,不能够靠眼、耳、鼻、舌、身直接感知,不能够靠观察直接把握,靠的只能是体验。假使到物质世界去直接观察,可能会背“道”而驰。魏晋玄学家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说:“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须出户;若其不知,出愈远愈迷也。”所以道家强调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使内心进入虚静、安宁的状态,以直觉式的顿悟把握事物的本体。
解读至此,海子心中要重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园,这样的家园有无可能重建,大家可能已有了自己的见解。
海子的诗,特别是短诗朴素异常,很少雕饰,大多朗朗上口,易于传诵。这种朴素中蕴涵与众不同的光辉,有一种直抵事物核心的力量。这既来自诗人对东西方元典文化的谙熟,也来自他对“大诗”写作的孜孜以求,如同《重建家园》所呈现的那样。
从现代汉诗的发展历程和海子所处的时代来看,他是一位有远大抱负和高迈理想的过渡型诗人。这里所谓的过渡,有以下三层含义。
首先,海子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不仅诗人的生存遭遇危机,而且也遇到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诗人身份的合理性不断受到质疑,这些质疑会连带地引起诗人的自我怀疑,诗人内心总是对既存的一切充满了怀疑。比如,做一个诗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写诗这种行为的意义到底体现在哪里,诗是能改变现实、拯救世界还是能救赎自我,等等。这些在以前并不会作为问题,至少不会作为严重的问题而存在。
在西方,不要说柏拉图时代,即使到了19世纪,英国文学家、哲学家托马斯 · 卡莱尔说:“诗人是世界之光。”美国思想家、诗人爱默生仍然赋予诗人以“君主”“帝王”的形象:“诗人就是说话的人,命名的人,他代表美。……诗人不是一个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他自有权力,使自己成为帝王。”布罗茨基认为:“诗人是文明之子。”但是在海子生活的时代,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经历了朦胧诗热潮后,诗歌不可避免地衰落,诗人从“抒情王子”一变而为遭人戏谑的小丑。海子恰好处在一个夹缝之中:从他的理想来说,诗人虽不再是从前代神立言的人,但他坚信诗人和诗歌仍然应该独享其尊严、力量和光辉。他是他的世界里“孤独的王”。这种夹缝状态也就是后现代所讲的“之间”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最尴尬,也是最痛苦的,他们要承受来自外部和自我内部的双重压力。当然,不是只有诗人才处于这样的状态,但唯有诗人对此最为敏感。某种意义上,是诗人表达了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想表达而不能表达的感受,诗人在替我们说话。海子又是在这样的压力和痛苦之中,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少数诗人之一。
其次,海子的诗歌写作处在从“我之诗”到“人之诗”的转换时期。新诗自诞生以来,成长历程中的一条主线就是有关“小我”与“大我”之辩:或执着于书写“小我”,或希求以“小我”见“大我”,或简单粗暴地以“大我”取代“小我”。就以当代诗歌的发展来看,十七年诗歌的总体态势是将“小我”与“大我”融为一体。20世纪60年代初,贵州诗人黄翔写了一首《独唱》,而在那个年代提倡“独唱”的人,无疑是异端。到了“文革”,主流诗歌里基本上是“大我”,那个代表政治意识形态的“我”压制、消灭了“小我”的存在。朦胧诗则重新恢复了“自我”在抒情诗中的合法地位,但他们在整体上确实存在以自我的体验来鞭挞非人的时代,呼喊出“一代人”心声的写作指向,扮演的是代言人的角色。再到第三代诗歌,更年轻的诗人普遍以拒绝做“时代的传声筒”自居,以沉醉于自我为反叛、先锋。进入新世纪后网络诗歌的兴起,强化了诗人自我情感的宣泄。那么海子呢,他一直秉持这样一种信念:消解类似于“小我”与“大我”的二元对立,返归人原始、本真的浑沌一体的状态;从诗的角度讲,就是要重建诗的家园。海子曾明确表述过他的诗歌理想,这就是人们熟悉的“大诗”理想:
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大诗”呢?它同样是一种结合,但不是“小我”与“大我”的结合,而是“民族和人类”的结合,是将本民族的情感特色与人类的普遍情感结合起来,以打破或弥合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灵魂与肉体、物质与精神等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简单地说,“大诗”理想就是“普遍诗歌”的理想,它指向人的存在,指向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的深处。就这样的诗歌理想来说,他站在了塔顶,视线越过了众人,所以他必然是孤独的、无人喝彩的。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都始于自我,但这仅仅是写作的开始,不是它的全部,更不是它的结局。
再次,从诗歌写作的精神指向和文本类型上来说,海子的诗处于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中间”状态。这种说法可能比较暧昧,却是符合实情的。一方面,古典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以情感抒发为最高原则,后者强调心灵的自由与表达的自由,不受一切清规戒律的束缚。此外,浪漫主义诗歌多取材于乡间、田野等。这些在海子的诗特别是抒情短诗中有鲜明的体现。另一方面,海子的诗借助自然的种种元素,形成了比较完整、独特的象征体系。这与象征主义诗歌又非常接近。比如瓦雷里的《石榴》、波德莱尔的《交感》等,通过对自然元素之间关系的描绘,形成一个象征世界,来映射人的本体存在。象征主义诗人在哲学观上受柏拉图“唯灵主义”的影响,认为世界可以分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本体世界即自我世界,现象世界本质上是自我世界的外在显现。诗人通过对可见可感的现象世界的表现,就可以象征性地表现真正的本体—自我。这个自我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与现象世界相对的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海子在他的绝笔《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将抒情诗人分为两类:一类热爱生命,但他热爱的是生命中的自我,认为生命可能只是自我官能的抽搐和内分泌;另一类虽然只热爱风景,但他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是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从热爱自我进入热爱景色,将后者当成“大宇宙神秘”的一部分,就出离了第一类狭窄的抒情诗人的行列。从这段论述来看,热爱景色使海子具有浓厚的古典诗人气质,而把景色当成“大宇宙神秘”的一部分来体悟,又体现出现代诗人对象征手法的热衷。至于为什么海子会走上这样一条独特的写作道路,就需要结合他的生平来分析。概括地说,海子进入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农村,对乡村、土地有深厚情感,是一位传统情结很深的诗人。与此同时,在广泛的阅读和勤奋的写作实践中,他深感单纯的抒情已无法达到构建“大诗”的意图;而“大诗”理想,内在地要求诗人尽可能融合一切有用的诗歌元素。海子的一只脚已经迈入现代的门槛,另一只脚仍然深陷在传统文明、农业社会的泥土里。
过渡型诗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难以复制。处于“之间”状态的诗人某种意义上是分裂的人,他们所承担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他们总是会为自己设定一个在常人看来无法企及的目标。就《重建家园》来说,海子秉持“绝圣弃知”的信念,渴望返归人原始、本真的浑沌一体的状态。海子为自己设定的这样一种理想追求,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要忘记,诗人的杰出之处,正在于他总是听从内心的律令或某种神秘的召唤,不可救药地去追寻那不可实现之物。萨特在评述马拉美时说,像马拉美、波德莱尔等诗人, “他们必须是不可救药的,必须心甘情愿不可救药,必须终生披麻戴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 韦伯则断言:“如果我们不是反复追求不可能的东西,那么我们也无法实现看起来可能的东西。”作为农民之子亦即“人之子”的海子,正是以他“重建家园”、重建诗歌理想的矢志不渝的信念,而不是结果,长久停驻在我们的视野里。
作者:魏天无,1988年本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为美国孟菲斯大学(UM)交换学者(2012—2013)。出版学术专著(合著)六部,评论集两部(含合作),随笔集一部。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pg电子模拟器试玩在线
本文由:PG电子模拟器家纺生活馆提供